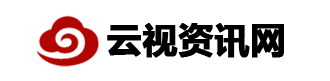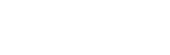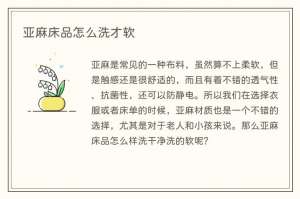一份底稿的震撼和一个读者的质疑
这次上海书展最吸引我的,是它为工具书开辟的专题展览厅,插架万轴,琳琅满目,大略呈现了近七十年来我国该领域的编纂出版成绩。说来惭愧,直到硕士二年级,我才因撰写论文之需而留心这类图书。《文史工具书概述》(赵国璋等著)、《校雠广义》(程千帆等著)等书指导我,遇到哪些问题可以查检哪些文献,从而避免对“百度”、“知网”及数据库的过度依赖。可惜的是,尽管工具书对读书治学不可或缺,学校却未设置相关课程,老师也少传授相关心得,以致一些学生直到毕业也没有充分重视和利用。我成为图书编辑之后,在工作中也发现一些原本借助工具书就可避免的疏误。比如“亲朋卒至”之“卒”,作者以为“同‘萃’”,意为“聚集”;其实应作“突然”解,音cù,又作“猝”,《世说新语》有“暴雨卒至”、“使者卒至”。再如“溟涨无端倪”,作者释“溟”为“海”,则“溟涨”似谓海涨;其实“溟涨”分别指“溟海”和“涨海”,二者均为古籍所记海名(见《十洲记》《梁书·海南诸国列传》等)。有位作者在引文“弟一流”之“弟”后括注:“应为第”,似说“弟”为“第”之误;其实“弟”正为“第”之初文,《说文解字》即以“弟一”、“弟二”排序……如果勤于并善于利用工具书,不难减少上述臆说通假、望文生义、以今律古等问题。我甚至认为,一部赅备精核、检索便利的工具书,足以“藏之名山,传之其人”,其价值不知胜于多少“重大课题成果”。比如我社出版的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(朱保炯等编),方便了多少明清文史学者!
言归正传。在工具书尤其是词典中,“古今兼收,源流并重”的《汉语大词典》久负盛誉,其内容之丰赡(汉字二万多个,词语三十七万余条,《订补》新收及订正条目达三万余),几可谓“没有查不到,只有想不到”,能够扫除文献阅读中的多数障碍。该书第二版编纂工程已经启动(第一册征求意见稿80%以上词条均有修订),计划于2025年完成。这次书展公布了第二版的部分底稿,我驻足观看良久,只见每页纸上,满面涂改,丹黄灿然,订补篇幅几与原稿相侔,一如学者江蓝生所说的“百衲袍”。底稿旁边是《编纂手册》《引书格式》《工作用表》,足见通盘规划之全与精,让我心中顿生敬意!爱惜名誉和字纸的古人,“恒遗恨以终篇,岂怀盈而自足,惧蒙尘于叩缶,顾取笑乎鸣玉”(陆机《文赋》),所以有“观天下书未遍,不得妄下雌黄”之诫(颜之推《颜氏家训》),又有“文字频改,工夫自出”之劝(吕本中《童蒙诗训》)。如果所有的作者、编辑都以这种严谨负责的精神对待作品,“灾梨祸枣”之诮,庶可免乎?
《汉语大词典》(第二版)编纂修订稿
《汉语大词典》(第二版)的《编纂手册》《引书格式》《工作用表》
老版本《辞源》《新华字典》等
工具书专柜
我在本社摊位值了两天班,切身感受到人们的不同阅读需求:有人一见繁体竖排就摇头,有人非要此种不可;有人喜欢简约淡雅,有人热衷图文并茂;有人执着古色古香,有人只要白话翻译;有人希望字大行疏,有人更重价格实惠……有趣的是,大概因为前阵子报道的华为公司产品取名多自《山海经》(所谓“几乎把整本《山海经》都注册了”),不少读者就专为此书而来,一时有供不应求之窘。这番经历能帮助我在编辑工作中更多地考虑读者因素。虽然连续站立六个小时深感疲惫,心中却有一种服务的快乐。唯独一位读者的质疑出人意料,他手持《中国史纲》(张荫麟著,收入《蓬莱阁典藏系列》)发出“三连”:“这书不是已经出滥了吗?怎么还出啊?浪费社会资源!”我只是笑笑,没有回答。我心里相信,是否“浪费社会资源”,不取决于同类书籍的多寡,而取决于编校质量及读者评价的高低。“人无我有,人有我精”——正是我社一向秉持的出版理念,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陆续推出的《蓬莱阁丛书》(收书五十余种,各附名家导读)至今仍能改版重印的根本原因。
1999年版《中国史纲》
2019年版《中国史纲》
有位衣着朴实的腼腆小哥,手持茶杯来到我社摊位,一口气买下5280元的《宋拓淳化阁帖》,并对我说,他从事高危性质的天然气行业,同时对图书很感兴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