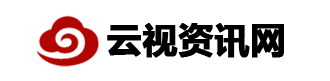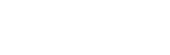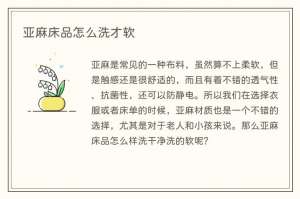2003 年春节,薛老师和蔡阿姨出来广州,住在番禺薛怡青家,她在洛溪新城买的房子刚装修好,叫我和老公过去吃饭,见到他们全家人。薛老师忧心忡忡地跟我说: “红影啊,你知不知道李菊岚去哪了?她把我的佳佳不知道带到哪里去了。”佳佳是他的大孙女,李菊岚是他三儿子薛学建的老婆,也是我初一的同班同学。我一头雾水,蔡阿姨就在一边叫薛老师不要再说了,转头看了看阿军,又笑眯眯地跟我说: “红影,你嫁得好啊,大妹里嫁给满仔里多好啊!”听蔡阿姨这么说,我也不敢打听他们家发生什么事了。吃完饭我邀请他们来家里,他们说不了,想回去五华了。
到了年底,我装修李肖峰新房的时候,在洛溪新城打电话给薛怡青,她叫我上去她们公司奥林匹克花园办公室坐,一套复式商住楼,是一家做通信设备器材的公司。快到中午的时候,她说请了阿姨回来煮饭,叫我试试她们的工作餐,言谈中, 她就感叹装修不好做,我想可能是以前经历过怕了吧。那时她也是结婚多年还没生小孩,她老公周冬斌是她的同学,是下坝人,跟日杂公司一桥之隔,听她说周冬斌经常会开车回去看望薛老师和蔡阿姨,子女个个都不在身边,广告店已经没开了, 毕竟年纪大了。
后来大家各有各忙就很少联系,都是通过朋友圈关注彼此的情况了,知道薛怡青生了女儿也是隔了好几年后在朋友圈看到,比我儿子小几岁。在薛怡青的朋友圈断断续续地知道李菊岚改嫁了,佳佳跟着她。
2016 年,薛怡青在微信上和我联系,说大侄女佳佳想参加艺考要先集训,问我哪家好?我说也不清楚,她可能是见我发过舅父是画家的信息,想当然地以为舅父是美院的老师吧。但她确实知道我在美院读过研修班,却不知道我那时跟美院的老师同学都没联系了。
她说佳佳的文化科成绩很好,但不知道考哪家学校好,如果考北京的清美或中央美院的话呢,又怕竞争不过北京户口的本地生。我说那干脆就考广州美院吧,她听了犹犹豫豫。于是我就在网上找了几个培训机构的资料给她看,她挑了一家说想去看看,叫我陪她过去,是在番禺那边的,于是我坐地铁三号线到厦滘站,她开车来接我,跟她已经多年不见。
薛怡青来厦滘地铁站接到我的时候,上了车,同时都说,“哎,好多年没见了, 还好吗?”她女儿刚上小学。我只说了一句,已经没开公司,也没做装修了,还一身病,她没问我得了什么病,我也就没再讲下去了。我问她是不是还在那家公司上班?她说:“是呀。”我说了句:“呵呵,老油条了。”她也没出声。
一路开车去到番禺一个很偏僻的旧厂房改造的园区里面,经过一个叫“汪晓舒”工作室的门口,后来才知道他是广州市国画协会的会长。我们按地址找到那家“围墙”培训学校的时候,培训班还没开始,正在招生阶段,但也很快就要开学了, 暑假就快到了。接待的老师先带我们去看了宿舍楼,教学楼。回到办公室接待厅才开始仔细地为我们介绍他们的学校,他们原来是在昌岗路广美后门江南大道附近的李振天工作室旁边,后来扩大经营,就搬到那个地方,出于成本考虑吧。
薛怡青一直都很细致地问这问那,从什么时候开始上课,都有哪些老师上课, 几月份联考,几月份校考,文化课怎么办,跟原来学校怎么配合等等……我根本都不用问什么了,就站在旁边稍微补充一下,那个老板见我们迟迟都定不下来,就说: “不是你自己的小孩,是很难定的了,你要叫她自己过来,还有小孩的妈妈亲自过来了解最好。”然后又叫了他们聘请的一个清华美院刚本科毕业的老师过来,又从头至尾跟她介绍一遍,我就也加了那个老师的微信。最后薛怡青说还是要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,临走前,她跟那个老板说:“我父亲是书法爱好者。”我急忙在一边说:“是长乐县的书法家。”老板听了,也不觉为奇,他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做成你这单生意。
在回去的路上,我当然意识到她是想,如果我跟她说跟广州美院的哪位老师或者教授很熟,她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来这里仔细了解了,人们都习惯了办事一定要找熟人才可靠。可我一直都没有出声,又经过市桥的时候,她打电话叫她二哥出来一起吃饭,在旁边听到薛天毅说,你们去吃就可以啦!我就说很怀念你们公司的工作餐哦。
于是她又带我上去她办公室,这次去到,她把我带上去复式的二楼总经理室,我刚有点迟疑,见她在里面很熟悉地把包挂在门后。才突然明白过来,原来她就是公司的总经理,休息了一下,我们下楼吃午餐。她把去了解到的情况打电话跟李菊岚说了一下,然后叫她自己带佳佳过来看。李菊岚不是很想来广州,觉得不方便, 说在深圳也有很多培训机构,不如找她大哥薛智鄂帮忙找熟人吧。吃完饭,薛怡青叫我上去休息一下再走吧,于是我又跟她上去一起休息,她把平时自己午休的沙发让给我睡,自己睡她的大班台,把被子铺在桌面上,从头至尾,她没多问我一句什么, 怕我难堪。
到了 2017 年,我听薛怡青说她爸爸也患了骨质增生,被折磨得很痛苦。就打电话跟他说:“薛老师呀,我舅父刚好就研发了一种可以治这个病的药贴,您要不要试用一下啊?是他自己研发的,还拿了国家专利的哦?”
“呵呵,那就寄过来试用一下吧。”他在电话那边笑着说,以为是我自己在做这个生意。
我问舅父买了一个疗程,买的时候,他说:“还是以前给你的那个价格。”我说: “阿舅,我是买来送给我以前长乐的老师的,能不能便宜点?”
舅父说:“大红,价格已经是按几年前的了,我再送一瓶喷的药酒叫他结合起来用,还有一瓶软膏抗过敏的吧。”于是,我叫他先寄过来广州给我看一下,又交代舅父以后也按给我的价格给薛老师。
寄回去长乐给薛老师,跟他们说:“正常要用两个疗程才开始有效的,我送一个疗程给他,试用了有点效果就继续直接跟我舅父买吧。”把惠州舅父的联系方式给了薛怡青。
隔了一个多月,薛怡青打电话给我说:“红影啊,没想到这个药贴是 500 元, 我妈说给回钱给你呀。”我跟她说:“不用了,一点点心意吧。”
在跟薛老师说他生病的事时,我告诉他已经没做设计了,就在家里照顾孩子, 听出他语气里的失望,就跟我说了一句:“哦,能把孩子照顾好就不错啦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