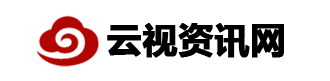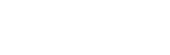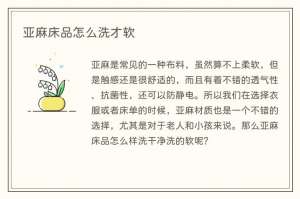我们家本来姓李,不姓张。我们是大城人,原籍河北大城县。
一九九零年三月,著名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在台北采访张学良时,张将军追溯了张家的渊源。
“那后来怎么改姓张了呢?”唐教授问道。
是这么回事,是张家的姑娘嫁到了李家,可是姓张的家里没有男孩子了,怎么办呢,就把我们李姓的男孩子抱了一个给张家,就这样姓了张。
后来,我把我们李姓的祖宗都找到了。我曾跟我父亲说。现在我们李家已没有人了,你干脆把我再过继过去吧,我父亲听后还连连说“好”,可实际上也没有再去做。
我降生的地名叫八角台,我实际上不是在地上降生的,我是在车上生的。你看,我的头上都有疤,就是在逃难的车上碰的。我小时候有病,身体很不好,还吐过血。那时我母亲又有病,没有奶吃,她就把那高粱米饭嚼碎了喂我。我没想到我还能活这么大岁数。
我原来不叫小六子,叫双喜,这个名字有点来历。
三岁那年,算命瞎子说我命太硬,克父母,必须到庙里许愿,做佛门弟子,才能消祸免灾。
母亲于是把我许到庙里去当跳墙和尚。什么叫跳墙和尚?就是许到这个庙里当和尚,然后再跳墙跑掉。
因为当了和尚,我就不叫双喜了,就把双喜做了个纸人放在庙里,我本人踏着一个板凳跳墙跑了。纸人的双喜就放在了庙里,这样我的名字就没有了。出庙时听到有人头一声喊什么,我的名字就叫什么,结果头一声听人喊一个小孩子叫小六子。我说笑话,那时如果有人喊王八蛋,那我的小名就叫王八蛋了。
我四五岁时,父亲归朱子桥管,已当上管带了,统领二百多人马,驻防在新民府,训练士兵。我是在新民府长大的。新民府离奉天一百二十里地,那里驻有日本兵。有一回,当兵的去玩妓女,双方打起来了,我父亲的兵被日本人打死了两个,父亲火了,非叫凶手偿命不可。那时由官府办案,一个兵给赔了五百两银子。父亲更火了,过了三天,父亲派人打死了三个日本人,一人赔了五百两银子。他说,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不就完事了嘛牎这事闹得很厉害。
不久,上头就把父亲调到辽源驻防,我原配就是那儿的人。在辽源,父亲给我请了个英文教师。这个人我现在很想念他,我到他那儿去念英文,先生对我很客气。你说这个英文怎么念吧,他是广东人,他老人家说广东国语,教我念英文nine(九),就发音念作“狗”。那时候念英文,旁边并没有中国字注解,那我以为就是“狗”了。后来又念dog,他说这是“犬”,我脑子想,这“犬”与“狗”有什么区别呢?我就想,nine可能是大狗。后来,慢慢地出现ninedogs,哎,它们两口子怎么堆到一块儿去了?后来才知道nine是“九”。我这就是说,先生对我这样的客气,我有许多是自悟,也不能说是自修。
我小时候是有点儿小聪明,也非常调皮。那时念书,我们共三个人,一个表弟,还有一个堂弟,我们就抓着苍蝇放在一个瓶子里,把粉笔碾成粉末,各人有不同的颜色,我是红的,你是蓝的,他是白的,苍蝇就在粉末里扑棱棱,满身是颜色。搞完之后,这就是我的兵了,看谁比谁抓得多。上课时,苍蝇坏透了,我们的老师是近视眼,坐在那儿看书,苍蝇飞来就落在他书上。他说,噢,这苍蝇怎么是红的,而且这红苍蝇还扑扑地弹下不少粉末,这是怎么回事?我们看见了这情景,都偷偷地笑,老师猜想一定是我们干的,后来就翻我们抽屉,把苍蝇都翻出来了,第二天就打手板。
白老师教了我近两年,他就跟我父亲说,你不要让你儿子念书了,他总不是一个念书的人,他要干什么,你就让他干什么好了。